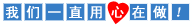- 阅读权限
- 90
- 积分
- 3000
- 在线时间
- 120 小时
- 精华
- 5
- UID
- 2620
- 性别
- 女
- 帖子
- 291
- 威望
- 3000
- 金钱
- 1371
- 注册时间
- 2007-7-20
 
升级    0% 0% - UID
- 2620
- 性别
- 女
- 帖子
- 291
- 注册时间
- 2007-7-20

|
有一段时间,大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缺什么”这个话题很感兴趣,谈论甚多。在2003年的杭州作家节上,它甚至成为几位作家“论剑”时的中心话题。陈忠实先生认为中国文学缺乏“思想”,张抗抗女士认为缺“钙”,铁凝女士认为缺少“耐心和虚心”,莫言先生认为缺乏“想象力”,鬼子先生则认为“什么都不缺”。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除了鬼子先生的剑走偏锋的高论宏议有些靠不住,莫言先生的说法有些简单,其他诸位的观点都有道理。我之所以说莫言“简单”,并不是认为他不该强调“想象力”的重要性,而是说他没有正确地说明我们缺乏什么样的想象力,没有正确地说明在怎样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积极地进行“想象”。在我看来,想象不是任性而随意的行为,而是服从一种更为内在的规范和纪律的制约,或者说,决定于观察的深入程度和体验的深刻程度;一方面,想象赋予观察以完整性,赋予体验以丰富性,另一方面,想象要想成为积极意义上的创造性的想象,就必须充分重视观察和体验的价值,必须使自己具备起码的事实感和真实性。
那么,我们的文学到底缺少什么呢?缺的东西很多,远不止几位“论剑”的作家所指出的那几点。在我看来,中国文学的问题是复合性的,而不是个别性的;是整体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大略说来,我们时代的相当一部分作家和作品,缺乏对伟大的向往,缺乏对崇高的敬畏,缺乏对神圣的虔诚;缺乏批判的勇气和质疑的精神,缺乏人道的情怀和信仰的热忱,缺乏高贵的气质和自由的梦想;缺乏令人信服的真,缺乏令人感动的善,缺乏令人欣悦的美;缺乏为谁写的明白,缺乏为何写的清醒,缺乏如何写的自觉。总之,一句话,几乎构成伟大文学的重要条件和品质,我们都缺乏。缺乏的结果,是我们有许多“著名”作家,有每年出版数千部长篇小说的数量,但却只有少得可怜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读许多当代作家的作品,我最经常的体验和最深刻的印象,是虚假和空洞,是乏味和无聊,每有被欺骗、被愚弄甚至被侮辱的强烈感觉。这些作家的作品不仅不能帮助你认识生活,了解人生,不仅不能让你体验到一种内在的欣悦和感动,而且,还制造假象,遮蔽真相,引人堕落,使人变得无知和无耻。
如果有人向我提出“中国当代小说最缺少什么”的问题,而且要求给出一个最重要的答案,那我的回答是: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人物形象,缺乏可爱、可信的人物形象。而这种缺乏是另一种缺乏导致的结果,即由作者缺少对人物的尊重导致的后果。是的,缺乏对小说中人物的尊重和同情,乃是当代中国小说的一个严重而普遍的问题。我们时代的一些小说家总是乐意任性而随意地描写人物,强迫他们说自己不想说的话,强迫他们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共同爱好,那就是,把人物置于尴尬的情境中进行羞辱。
众所周知,在现代文学的整体构成中,小说乃是一种具有主宰意义的文学样式,因此,说一个国家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小说中,应该是可靠的判断。而决定一部小说价值之大小、成就之高低的重要因素,则是看它是否塑造出了丰满、生动、不朽的人物形象。乔治•桑说:“一本小说如果不写人就算不上小说。”她说得对。人物形象确实是小说艺术的核心问题,也是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最感兴趣的问题。很多时候,读者读完一部小说首先记住的是人物。人物的爱与恨、悲与欢、离与合、生与死的情感历程和命运遭遇,紧紧地吸引着读者,让他们为他高兴,为他忧伤,为他庆幸,为他叹息。他们谈论他,就像谈论自己的朋友,自己的邻居,自己的亲人。某种程度上讲,一个民族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它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我们讨论一个民族的文学,等于在讨论一系列人物形象。如果说研究俄罗斯文学就意味着必须提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那么,研究者同样无法不提的是一些同他们的创造者一样重要的人物的名字:安娜•卡列尼娜、列文、渥伦斯基、玛丝洛娃、娜塔莎、安德列、拉斯柯尔尼科夫、梅斯金公爵、瓦尔瓦拉和卡拉玛佐夫兄弟。
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时代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显得虚假、委琐、丑恶,而俄罗斯作家笔下的人物总是那么可信、可爱甚至美好?通常,在俄罗斯作家笔下,即使那些人格残缺、灵魂丑陋、情感扭曲的人物,也不失其正常,也不乏值得你同情和怜爱的地方。这又是为什么呢?例如,在果戈理的对俄罗斯社会和民族性格中的残缺和病象进行尖锐讽刺和无情抨击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也是卑污之下的纯洁,是病象之下的健康,是耻辱之下的尊严,是无情之下的温柔。他的讽刺无疑让人发笑,但他决不把讽刺变成对人的诅咒和侮辱,相反,他最终要你体验到的是温馨和感动。正像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果戈理作品的一个特征就是“那总是被悲哀和忧郁之感所压倒的喜剧性的兴奋”。他说,“果戈理君把你那深刻的人类情感,崇高的火炽的热情,和可怜的劣等人的习惯感情加以比较,说道:他的习惯感情比你的热情更有力、更深刻、更持久,你站在他面前,会瞠目不知所答,像答不出功课的学生站在老师面前一样!……呵,果戈理君是一个真正的魔术家,你设想不出我是怎样生他的气,因为他差一点使我为他们哭了,他们只是吃、喝,然后就死掉!”在别林斯基看来,果戈理虽然也尖锐地揭露丑恶,但他在描写人物的时候,从来就不曾放弃“诗意”和“公正”这两个尺度。他说:“如果果戈理时常也故意地嘲弄一下他的主人公们,那也是不怀怨毒,不怀仇恨的;他懂得他们的委琐,但并不对此生气;他甚至还喜爱它,正像成年人喜爱孩子游戏,觉得这游戏天真得可笑,但并不想参与到里面一样。可是,无论如何,这依旧是幽默,因为他不宽恕委琐,不隐藏、也粉饰它的丑恶,因为一方面迷醉于描写委琐,同时也激发人们对他的厌恶。”他高度评价果戈理在人物塑造上所取得的成就,所带来的能“对世道人心发生强烈而有益的影响”的“纯洁的道德性”。他甚至动情地说:“呵,在这样的道德性前面,我是随时准备屈膝下跪的。”
是的,纯洁的道德性,果戈理作品打动我们的心灵的力量就来自这一点。它包含着善良与悲悯。它充满帮助有缺陷的人摆脱困境的诚意。我们从这些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果戈理的眼神,它流露出是对人物的期待,它似乎在告诉两个吵架的伊凡,只要心胸再宽广一些,你们就可以相安无事的;它似乎在告诉读者,可以厌恶小说中所写的事,但是不要讨厌做那些事的人,更不要恨他们,因为他们之所为固然不雅,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它似乎在告诉所有的人,我们应该活得更健康一些、更高尚一些、更诚实一些、更美好一些。
相比之下,我们时代的文学就显得冰冷而阴暗。除了汪曾祺、路遥、陈忠实、史铁生、张洁、宗璞等少数作家,我们的相当一部分小说家就缺少俄罗斯作家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的温暖的爱,缺少纯洁而健康的道德性。他们不知道尊重人物,甚至不拿他们当人看,变着法儿虐待他们,羞辱他们,直到把他们身上最后一点人格尊严剥夺干净,直到把他们内心深处的最后一丝善念变成仇恨。中国的几乎所有的自命不凡的“先锋”作家和失去道德感的“消极写作者”,都不知道善待自己笔下的人物,而是把他们当作没有疼痛感的物件来糟蹋。暴力和仇恨,欲望和放纵,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主题。遗憾的是,他们仅仅满足于把人降低为兽欲或本能的奴隶,而缺乏将人如其所是地描写出来的能力,更缺乏将人进行升华性叙写的能力。
余华,这位文学素养并不高,思想并不成熟,体验资源并不丰富的“先锋”作家,虽然像残雪和莫言一样,被中国及外国的一些批评家吹得神乎其神,但却不知道按正常、健全的人性尺度叙写人物。残忍的暴力伤害是他喜欢表现的主题。尖刀和利斧等凶器是他写小说时须臾不能少的道具。他把殷红的鲜血涂满了一切能涂抹的地方。他把人物的内脏掏空,把自己的沾满鲜血的浅薄而简单主题填塞进去。《现实一种》是一篇给余华带来不少掌声和鲜花的小说。但正是这篇怪异的小说,体现着余华作品的变态与畸形,表征着他对人物的褊狭的理解和残忍的肢解。在这篇做作、虚假的小说中,你可以看到对人物行为的罗伯-格里耶式的描写:山岗和山谷兄弟以及他们的妻子,仿佛四棵会行走的树,仿佛四块会行动的石头,只有简单的动作,而没有情感和思想。小说中的孩子也像大人一样残忍。皮皮从堂弟的哭声中,“感到莫名的喜悦”,于是,他通过打耳光和卡喉管,来“如愿以偿”地听堂弟的“嘹亮悦耳”、“充满激情”的哭声。这个叫皮皮的孩子终于把堂弟掐死了。接着,他又被叔叔杀死。叔叔又被皮皮的爸爸杀死。皮皮的爸爸又被依法枪毙。他的奶奶随后也死了。
余华完全无视情节的合理性,无视人物的情感的复杂性,只管冷漠而简单地让人物互相伤害。他的叙述夸张而虚假,幼稚而粗糙,不仅令人难以置信,不能引发人的积极的道德反应和审美感受,而且还引起人极其别扭、恶心的生理反应。他对那位三十来岁的女医生解剖山岗尸体过程的叙述尤其残忍、冷酷和虚假。作者细致地描写“山岗的皮肤被她像捡破烂似地一块一块拣了起来”:“失去了皮肤的包围,那些金黄的脂肪便松散开来。首先是像棉花一样微微鼓起,接着开始流动了,像是泥浆一样四散开去。于是医生们仿佛看到了刚才在门口所见的菜花地。”在余华的叙述中,解剖尸体对这些穿白大褂的人们来讲,像轻松地做游戏一样让人快乐。他用“赞叹不已”、“微微一笑”、“非常得意”“兴高采烈”、“妙不可言”等词语形容医生解剖尸体时的心理体验。然而,这样的描写是不可信的。它与人物无关。它不过是作者对自己的混乱而恣肆的想象的描述而已。
另外一个在小说中任性而粗暴地对待人物的当代小说家是贾平凹。虽然我对这位小说家的作品已多有批评,但他的作品中依然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尽管这样做有可能招致别人的误解,会让人说你“也许急了”,会让人说你因为怀疑作家是“偷斧头的”才抓住人家不放,才心怀叵测地批评人家,但我们必须坦然地面对这些可笑的误解,就像我们要享受夏夜的清凉就得忍受蚊虫的叮咬一样,就像一个内心无愧的人敢于平静地面对上天的雷鸣一样。
是的,贾平凹小说作品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尊重人物。他拿人物当玩偶,当道具,随意驱遣他们,随意摆布他们。他用自己的情绪、趣味、思想作材料,织成厚厚的幕布,将人物的面孔遮蔽起来,将人物的身体裹缠起来。他只写人物的话语和动作,而不写人物的心理和思想。在他笔下,女人随便就会跟一个不三不四的男人,往随便什么地方跑,或随便干不三不四的男人要她干的莫名其妙的事情。这位多产而著名的小说家,似乎根本不关心人物的其行为其来有自的动机和可能造成的后果。作者的任性和随意,造成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含混和外在形象的模糊。他的许多小说中的人物留给读者的印象,毫无清晰、生动的风貌,就像一堆在开水锅里煮过头的劣质香肠。《废都》是这样,《怀念狼》是这样,《病象报告》是这样,《阿吉》、《饺子馆》、《库麦荣》、《玻璃》、《阿尔萨斯》和《读<西厢记>》等中短篇小说也是这样。
《猎人》是贾平凹近几年创作的最能反映贾氏在人物叙写上的问题的一篇作品,我们可以通过对这篇作品的解剖,来考察贾氏小说写作中存在的缺陷和病象。
刊发于《北京文学》2002年第7期上的《猎人》,是一篇结构和主题都很混乱的失败之作。作者把男女之间的轻薄的调情与戚子绍三次被狗熊“干一下”的荒诞情节搅拦到一起,编造出一个匪夷所思而又令人大倒胃口的无聊故事。你从作者的叙述中体验到的不是高雅的趣味,体味到的也不是深刻的意蕴,而是大失所望的沮丧和被人戏弄的懊恼。事实上,被戏弄的不只是读者,还有人物。
读完这篇非同寻常的小说,我绞尽脑汁地想了又想,试图弄明白作者意欲表达的思想与主题。遗憾的是,我并没有找到让人略感满意的答案。我最后的结论,可能会让大家失望和沮丧,但是,没有办法,我得坦率而诚实地说出真相:《猎人》里根本就没有有价值的思想,或者,准确地说,这是一篇既没有好的故事,又没有深刻的主题的小说。事实上,我可能一开始就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一篇不拿人物当人看的小说,是费不着拿它当小说看的,即使其中真的有奇异、玄妙的思想,我们也应该站在文学和人道的立场,鄙弃这些与人的命运和尊严毫无关联的思想。
爱伦堡在评价契诃夫的时候说这位大师“连无人性的东西都能合人性地表达出来”。爱伦堡准确地揭示了契诃夫普遍受人喜爱和尊敬的原因。事实上,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写人,赋予人以人性的高贵和尊严,这几乎是所有那些真正的文学大师共同的特征。正像莫洛亚在《最伟大的》(1960)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为了吸引和打动人的心灵,作家必须对他们(人物)怀有真正的情感”;“真的,所有的伟大作家,从塞万提斯到托尔斯泰,他们的成就正在于善于塑造一些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都使人心疼的主人公”。我曾在批评阿来在《尘埃落定》中不知善待人物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没有热情,没有对于人物的朴素而热烈的爱,一个作家永远不可能真正地了解人,不可能完整而真实地写好人,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他常常会丧失对于高贵与卑贱、正义与邪恶、美好与丑陋的感受能力与分辨能力,从而使自己的写作成为缺乏可靠的人道原则和可靠的道德立场的消极写作。”
是的,同情、尊重甚至疼爱自己笔下的人物,是任何一个小说家写出真正的小说作品的前提条件。然而,我们时代的许多小说家似乎并不这么想。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的,是作者对人物的冷漠和粗暴。他们似乎更乐意以夸张、粗野的极端主观的方式,渲染人物身上的兽性和内心深处的黑暗面,试图借此显示一种时髦而浅薄的“先锋”姿态。而我之所以尖锐地、毫不宽假地批评余华和贾平凹等人在人物塑造上存在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觉得有必要坦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有必要不加讳掩地指出我们时代的作家在小说写作上存在的局限和不足;就是因为我想表达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小说是以批判、质疑的态度揭示人的艰难的生存境况的艺术,但也是以积极的态度肯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行为,因此,只有那些最终能让人意识到人性的高贵和尊严的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同样,只有那些能写出人性的高贵和尊严的作家,才是值得人们尊敬和感谢的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家;就是因为我想指出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除非克服自己在塑造人物时的任性而冷漠的态度,否则,谁也别想写出既活在纸上又活在读者心中的不朽的人物形象,谁也别指望自己的作品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大放光辉。 |
|







 狗仔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08-4-1 13:41:05
发表于 2008-4-1 13:41:05
 QQ空间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腾讯朋友 淘帖
淘帖 分享
分享 收藏
收藏 支持
支持 反对
反对 提升卡
提升卡 置顶卡
置顶卡 沉默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变色卡 显身卡
显身卡

 能加之于贾平凹头上吗? 汗。。。。寒。。。
能加之于贾平凹头上吗? 汗。。。。寒。。。